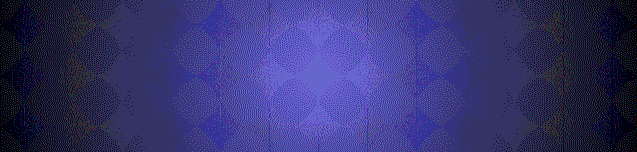
在经历了彼此隔绝的疫情生活后,短暂地走出家门、肉身在场成为人们迫切的追求。
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3年第一季度,国内旅游总人次为12.16亿,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.86亿人次,同比增长46.5%。五一假期期间,全国国内游达2.74亿人次。近来备受热议的“特种兵式旅游”、“Citywalk”与高居豆瓣热门小组榜的“报复性旅行协会”,也在向我们展现着旅游正如何被我们关心与讨论。
 图片来源:小红书
图片来源:小红书
有趣的是,在特种兵式旅游这一强调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、多景点、少花费的旅游方式走红之后,以慢速度、闲散漫步为特征的City Walk继而出现,这似乎预示着周密的规划又逐渐回归于“浪漫壮游”式的闲逛。
即使这两种旅游方式看似截然不同,却都牵涉到偏离常规这一目的。在长期关注旅游领域的人类学家约翰·厄里(John Urry)看来,“通过旅游,人可以有限度地摆脱例行事务和日常活动,让感官投入一连串刺激活动,与平日的平凡无奇形成强烈对比。”如今,旅游不断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展露新的面貌,它似与过往的浪漫壮游挥手告别,但又不断弥漫出怀旧的情绪。

早在前现代社会,西方社会便有了组织性的旅游。不过,那时的旅游,常指向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,它只被精英人士所独享,而平民依旧囿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内。
最初,旅游的出现与宗教密切相关。13、14世纪,朝圣成为普遍的现象,它混合着宗教、文化与娱乐,成为一种非标准化的旅行。17世纪末,壮游(Grand Tour)在贵族、士绅之间蔚然成风,此时它又强调旅途带来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熏陶。
直到19世纪下半叶,旅游才开始民主化,强调风景观光和个人体验的浪漫壮游(Romantic Grand Tour)开始兴起,彼时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让情绪与感受越发被重视,人们开始追求愉悦的体验。另一方面,铁路这一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,让平民百姓也得以搭乘火车外出度假。
在中国,旅游也经历了平民化的过程,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。历史学家柯丽莎(Elisabeth Köll)在《铁路与中国转型》一书中指出,好几百年时间里,中国人都在前往各个具有宗教、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地方旅游——商人们进行长距离贸易,官员们的职责也包括在帝国的各处领土上巡行。当时旅行的风险较高,也并不便利,人们为了降低风险,会翻皇历找一个黄道吉日出行,还会向路神进献贡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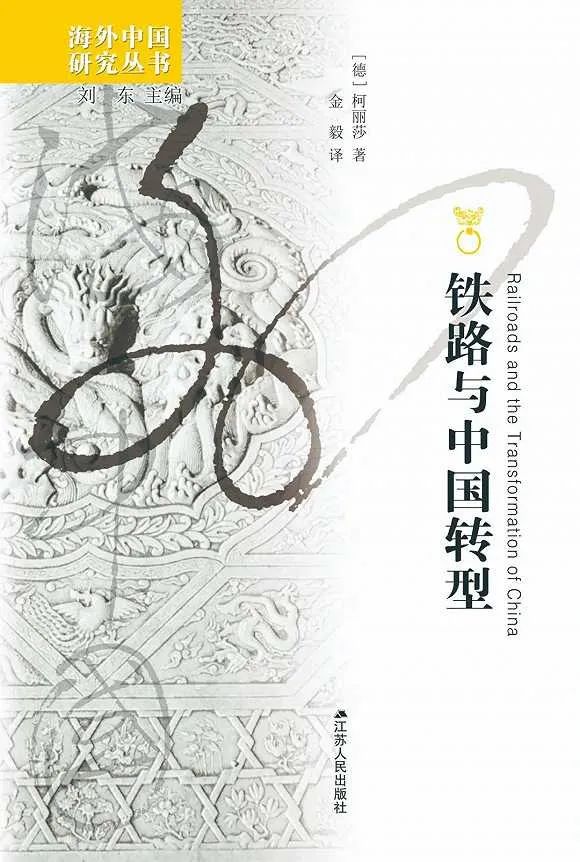 《铁路与中国转型》[德]柯丽莎 著 金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-2
《铁路与中国转型》[德]柯丽莎 著 金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-2
在宋朝,旅游展现出商业化的趋势,出现了和朝圣相关的旅行团、商业旅游安排以及导游服务。柯丽莎发现在这一时期,“宗教朝圣向普通人,特别是妇女,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,让她们能够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的限制,尤其是逃出男人的监视,到外面去旅行。”
民国早期,随着中国第一批铁路的启动,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容易。旅客们开始乘火车离开家乡,去往外地进行商贸活动或者学习。在休闲之余,旅客也将旅游赋予与工作、教育或者家事相关的任务。学者李思逸甚至在《铁路现代性: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》一书中提出,“铁路旅行作为一种现代经验的发生,与文学展开的互动,对民国时期的主体建构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。”
直至今日,随着高铁、飞机等交通方式不断普及与媒介技术的迭代,人类的地理移动更加便利,人们的出行与流动已成常态。我们正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 鲍曼(Zygmunt Bauman)所观察到的那般,进入流动的现代社会,这对旅游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。

在《铁道之旅》中,德国文化研究学者沃尔夫冈·希弗尔布施提出了“机械化旅行”的概念:“通过铁路的个体旅游,个体旅客被吸纳进了一个移动货物的有形系统中。”换言之,现代交通工具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旅游体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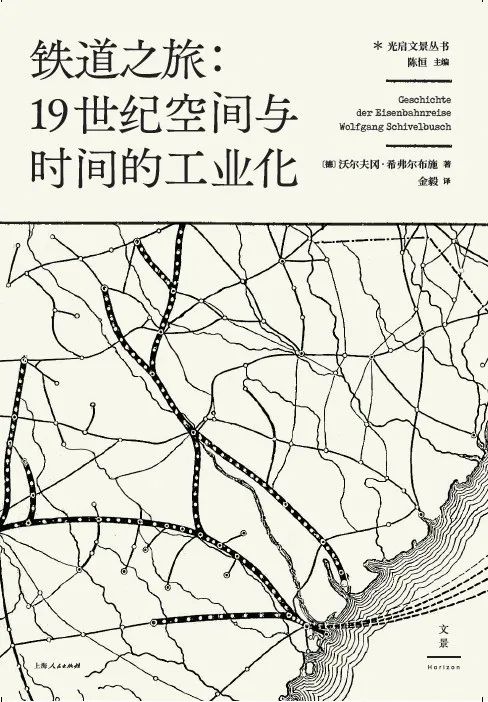 《铁道之旅: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》[德]沃尔夫冈·希弗尔布施 著 金毅 译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-7
《铁道之旅: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》[德]沃尔夫冈·希弗尔布施 著 金毅 译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-7
一方面,过去人们在使用低速的、劳动密集型的始生代交通技术时,沿途的景观是可以慢慢欣赏的,但在现代的旅行方式中,旅客对于沿途景观的感知,经由火车这类集成机器过滤,途中的空间被略过,只留下出发地、目的地这样的节点。
另一方面,现代交通工具通过座位安排与新的知觉强制实现机械化,通过运行图与不会偏离的路径实现例行化,使得“旅客经历的体验,与军事系统化有异曲同工之处”,而这加剧了旅游的“机械化”。乘客不再能切实感受到他们穿越景观的气味、声音以及通感等,而这些都曾是旅行的一部分。

徐志摩在《沪杭车中》(1923)这首关于火车旅游的诗作中,描述了现代交通工具如何打破“传统的旅行空间”,速度又是如何作用于感官体验的:
匆匆匆!催催催!一卷烟,一片山,几点云影,一道水,一条桥,一支橹声,一林松,一丛竹,红叶纷纷:艳色的田野,艳色的秋景,梦境似的分明,模糊,消隐,——催催催!是车轮还是光阴?催老了秋容,催老了人生!
对于旅游与速度的关系,沃尔夫冈甚至断言,“旅行是否会变得无趣完全与旅行的速度成比例。”速度的增加产生了大量需要视觉进行处理的可视影像,这不仅会增加游客的疲惫感,更可能使得旅行者的凝视转向代替品的景观,如书中的景观。
当下,旅游加速已经成为事实,“特种兵式旅游”应运而生。游客们挤出有限的时间,从一个航站楼、高铁站赶往下一个交通枢纽,穿梭在世界的各个空间,疲惫感自然被加码。更进一步的,“书中的景观”变成了“手机里的景观”,“独特的沿途风光”也被“可复制的打卡点”所取代。
在《游客的凝视》中,这种现象被约翰·厄里与乔纳斯·拉森归结为“后旅游主义下‘光晕’逐渐失落”。随着旅游的产业化,全球旅游景点数量攀升,就连平常活动的场所,皆以旅游模式加以重整和规划,宛若主题环境一般,但随之而来的是,旅游景点的同质化,旅游活动也越发单一,呈现“反光晕”的后果。于是,有人怀旧般地追忆起“城市漫步”(City Walk),试图在不预设目的的漫步中重寻浪漫。
 《游客的凝视(第三版)》[英]约翰·厄里 [丹麦]乔纳斯·拉森 著 黄宛瑜 译格致出版社 2020-9
《游客的凝视(第三版)》[英]约翰·厄里 [丹麦]乔纳斯·拉森 著 黄宛瑜 译格致出版社 2020-9
但无论如何,如今的游客越发清楚,观光旅游的本质变成了商品,要出门旅游,他们就得一次又一次地排队。人们也明白,他们不过是大众消费者中的一员,他们在网上找的旅游攻略、手里拿的景点介绍,不过是包装精美的流行产品。

“垮掉的一代”代表作家杰克·凯鲁亚克曾一次又一次书写旅行,在他的笔下,路上的癫狂不是目的,而是把灵魂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获得精神再生的方式。
《在路上》中,主人公萨尔在困顿之下,抛弃校园的闲荡生活,跳上沿途卡车,浪迹于66号公路。一路上他与伙伴痛饮,高谈东方禅宗,走累了就挡道拦车,夜宿村落,在疯狂的公路之旅中,诠释对虚无的叛逆。《达摩流浪者》中,主人公雷蒙背上背包,遇上引路人贾菲,他们一边禅修一边醉生梦死,也潜行于旷野、纵情“雅雍”与马特峰、孤凉峰的超拔洗涤,发出“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”的感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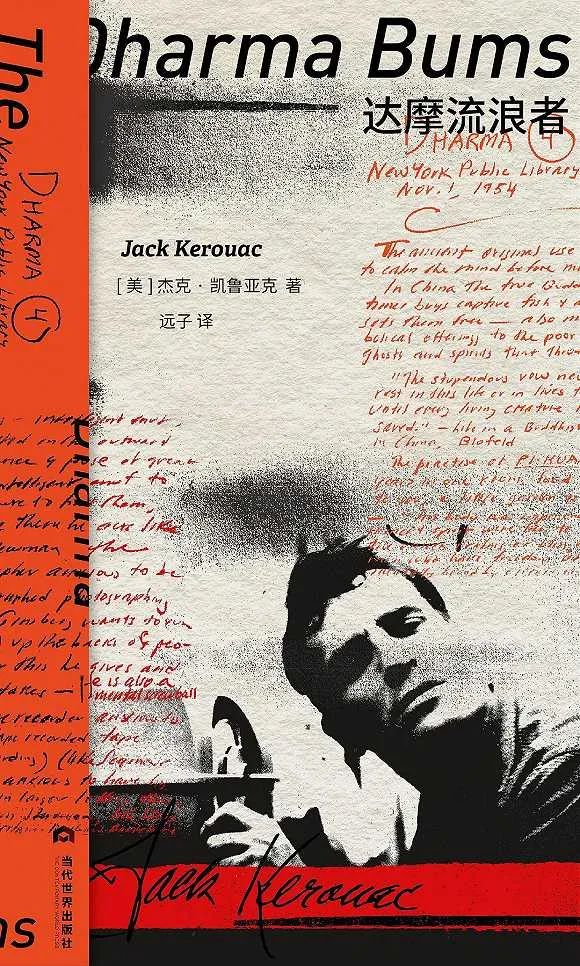 《达摩流浪者: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纪念版》[美]杰克·凯鲁亚克 著 远子 译一頁folio |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-3
《达摩流浪者: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纪念版》[美]杰克·凯鲁亚克 著 远子 译一頁folio |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-3
凯鲁亚克的“在路上”之旅,掺杂着失望、迷茫,也构成了一次盛大的逃脱。这种逃脱与今日的旅行不尽相同,但又彼此相连。如果细读关于特种兵式旅行的讨论,不难发现其中喘息的意味——面对无尽的事物与有限的时间,人们报复性地安排上一个又一个景点,“快、准、狠”地远离让人焦虑和疲惫的日常生活。
同时,“报复性”也暗示出对封闭生活的逃离。在过去三年的疫情生活里,人们困于自己的一方空间,面对远方的风景只能虚拟在场。正常秩序的回归,让人们高呼“我要把我失去的三年统统拿回来”,并像不知疲惫一般,一次次启程报复式旅行。City Walk则更似一种积极的抵抗,它尝试识破如今机械化旅游的真面目,执拗地通过漫步,切身感受城市,与人重逢。
如今的旅游或许不再是发生在特定时空内的纯粹体验,而颇有一些“符号经济”的意味,就像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乔纳森·库勒(Jonathan Culler)所描述的那样,人们“四散各地,分头寻找各式各样的符号,非要见识法式作风、典型的意大利举止、代表性的东方景致、标准的美式高速公路、传统的英式酒吧。”但当人们用“打卡”的方式打量眼前的景致,却也流露出一种不屑——人们不再能被景观震慑,因为它早已失去了光晕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呢?
(文章来源:界面文化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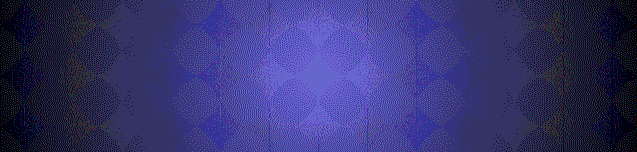
 图片来源:小红书
图片来源:小红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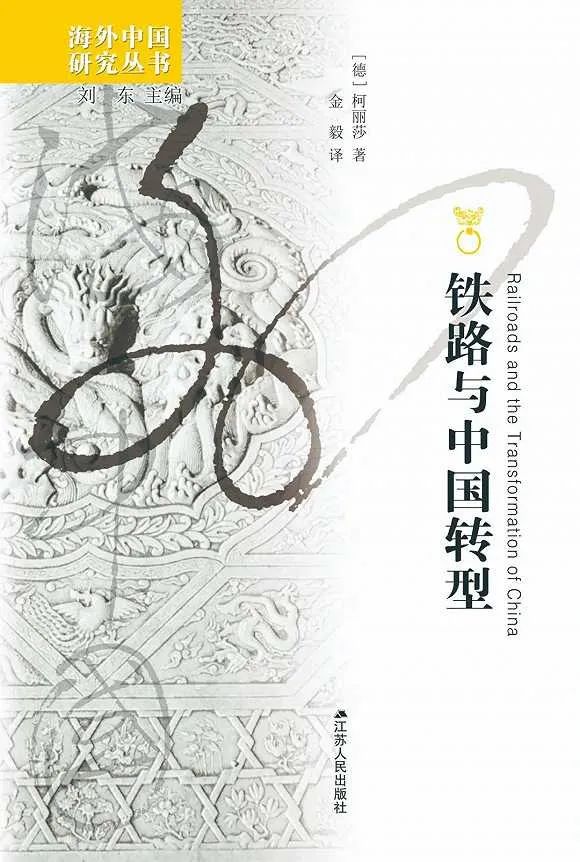 《铁路与中国转型》[德]柯丽莎 著 金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-2
《铁路与中国转型》[德]柯丽莎 著 金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-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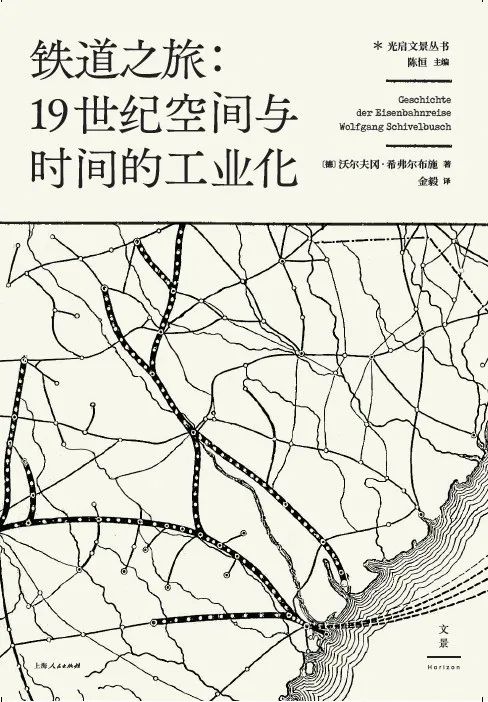 《铁道之旅: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》[德]沃尔夫冈·希弗尔布施 著 金毅 译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-7
《铁道之旅: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》[德]沃尔夫冈·希弗尔布施 著 金毅 译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-7
 《游客的凝视(第三版)》[英]约翰·厄里 [丹麦]乔纳斯·拉森 著 黄宛瑜 译格致出版社 2020-9
《游客的凝视(第三版)》[英]约翰·厄里 [丹麦]乔纳斯·拉森 著 黄宛瑜 译格致出版社 2020-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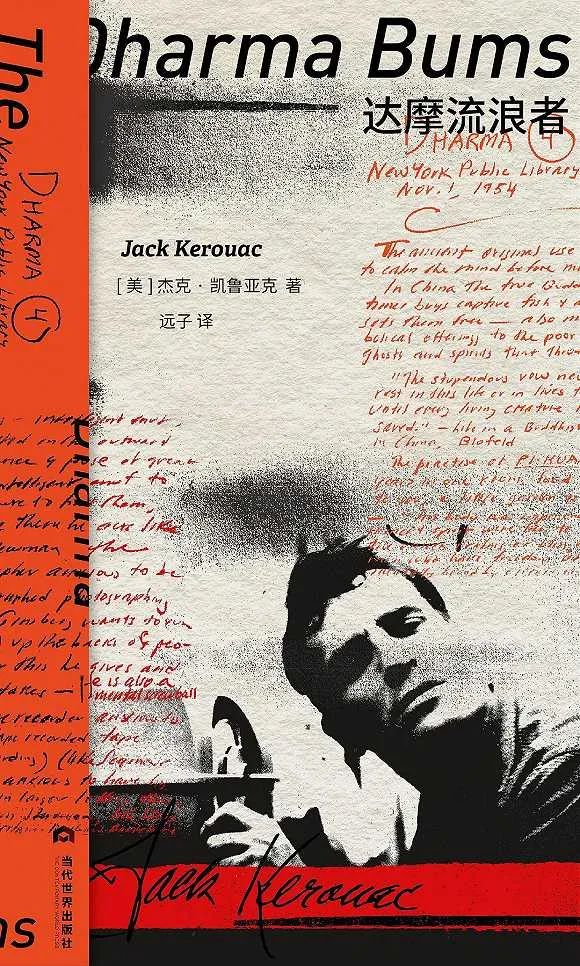 《达摩流浪者: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纪念版》[美]杰克·凯鲁亚克 著 远子 译一頁folio |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-3
《达摩流浪者: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纪念版》[美]杰克·凯鲁亚克 著 远子 译一頁folio |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-3

